黄干宗(黄干简历)
推荐文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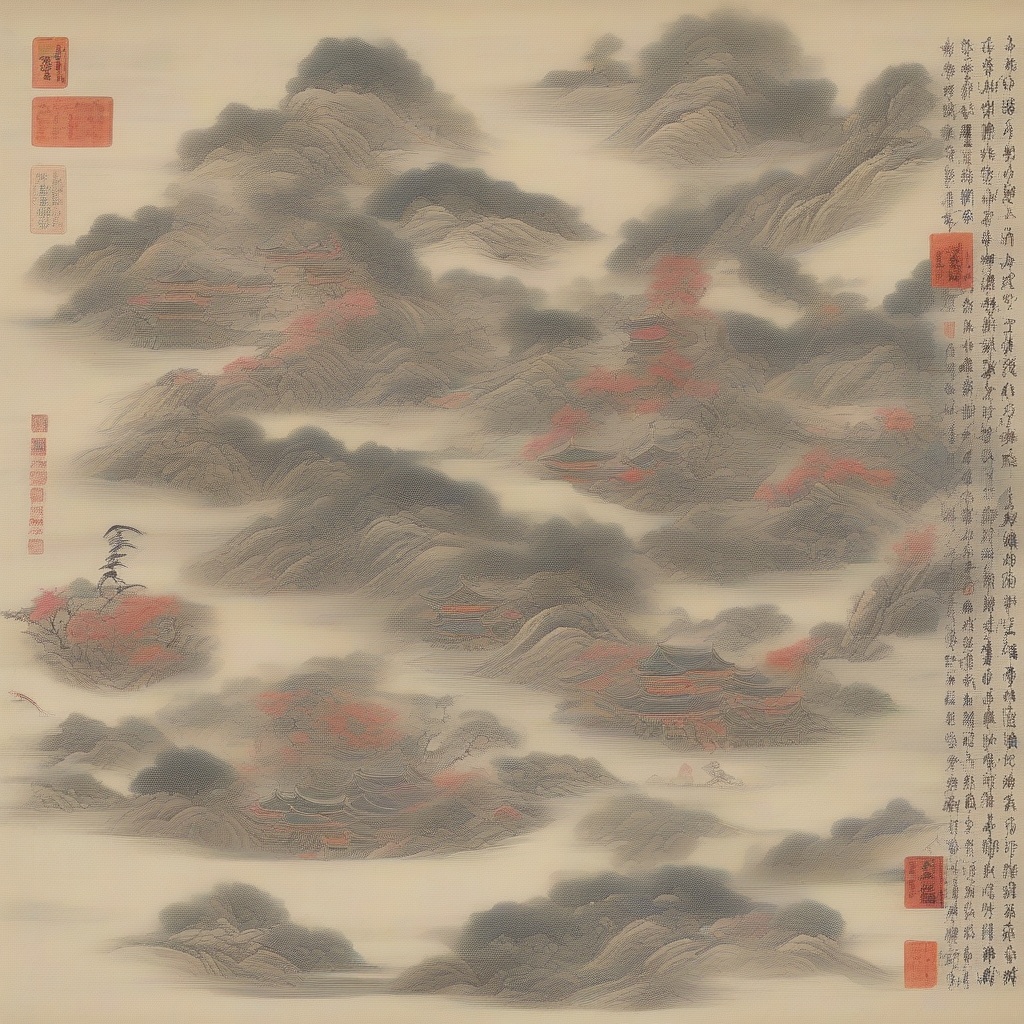
原载于《五台山》杂志2021年第8期
从哪里说起呢?
就从牛背上的夕阳说起吧!
黄干宗(黄干简历)
空气四周弥散着青草的味道,我知道这种味道是从一捆捆青草上散发出来。那辆破旧的牛车上装满这种青草,草上长满米粒似的花苞,草杆透出绿绿的光亮,那种淡淡的甜味从绿色的光亮中弥散过来。
我骑在牛背上,大口吸着青草的味道,眼睛却一直盯着将要落入西山的夕阳。牛背平展展的,就像隔壁翠婶的肚皮。翠婶总爱抱起我,将我的小屁股放在她平仰的肚皮上,然后摇着我幼小的双手,用嘴巴去亲,嘴里还一个劲地呜呜叫道:吃了你这个小亲亲,吃了你这个小牛牛……
翠婶有三个女儿,没有长牛牛的儿子,就认我做干儿子。干儿子没吮吸过干娘一丁点乳汁,却能坐在她的肚皮上撒娇,一摇一晃的,很像老牛的脊背。
西天的夕阳染红了半个天空,红彤彤的云彩像火塘里柴禾燃烧的火焰,可惜火焰却是凝固的,没有火焰舔舐锅底时一闪一闪跳跃。细细看,那云彩又不像火焰,有了别的形状,像牛,像马,也像三奴奴的黄毛头发……我正发挥着自己稚嫩的想象力将另一片云彩想象成别的东西,爹却扬起皮鞭,驱赶着身边慢腾腾的老牛。
爹说:天又烧了,明儿又是一个好天气!
我们这里说晚霞就说“烧”,好像那云彩能燃烧似的,要不爹也不会说,天又烧了。
爹赶着牛车,拉着青草,我骑着我家那头二岁口的小牛,就这样在爹悠长的喊牛声中慢腾腾地走向村子。
不远处的老河映满了落日前的晚霞,天水之间一抹黛青色的山横挡在中间,雾糟糟的什么也看不清楚,可那河中汩汩流淌的水声却仿佛回荡在耳边。我知道,我是很喜欢到那条老河边玩耍的,可爹除了饮牛时,让我和他一起靠近河岸,其余时间就像将我套上了缰绳,紧紧地将我拴在他的身边。爹说,那河里可盛货哩,你小狗日的要是跌了河就再也见不到翠婶了!
爹怕我一个人去河边耍水,就将我家二岁口的牛犊子训成了一头能骑的牲口,借此吸引我的兴趣。每到他上山放牛时,就将我抱上牛背,让我骑在平平展展的牛背上,他嘴里还一个劲地戏我,骑牛顶如坐轿,跌下来小心放炮!
我不知道,爹为啥总爱提起翠婶,就连翠婶亲我时,爹的眼睛里也会流露出水一样的东西。也许除了提翠婶,他再没有能够提起的女人。
从我记事起,就知道自己是没娘的孩子。娘哪去了,爹从来没跟我说过。听村上人说,我本来就没娘,是爹抱养来的孩子,爹从来没有娶过婆姨,在三十岁的时候就抱养了我。爹为啥不娶婆姨,却偏偏抱养我,村上人好像说,爹是为了翠婶。我只知道自己有爹,却不知道其他孩子为啥多出一个娘来。每天晚上爹搂着我睡觉,摸着大平展展的胸脯,我就很满足地睡去了。翠婶家的三奴奴总爱在我面前炫耀说,她晚上躺在她娘软绵绵的怀中睡觉。我没有娘,自然觉得她的话大不可信。爹的胸脯硬邦邦的,硬得像石板街上的石头。可自从翠婶将我放在她肚皮上摇来摇去,我才知道三奴奴的话没错。那以后,我就对三奴奴不无遗憾地说,要是翠婶是我的娘,那有多好啊!
翠婶认我作了她的干儿子,翠婶的丈夫三叔却对我爱答不理的,好像我偷吃他家的黄干馍馍。我才不管他理我不理呢,我爱坐的是翠婶的肚皮,爱听的是翠婶爽朗的笑声,爱吃的是翠婶的老南瓜,三叔是个大男人,胡子茬比我爹的还硬,嘴里的气味比我爹的还臭,我没摸过他干瘦的胸脯,一定比我爹的还硬。他不愿理我,我才不愿搭理他呢。
牛车走进村子后,西天的夕阳已经落到了山的背后,屋顶上弥散下来的青烟混杂着街巷里牛羊粪便的膻味,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。我吸着这种柴禾烧出的烟气,心里想着,翠婶家的锅里一定冒着热气,说不定这阵她家的饭已经做好了。这一点爹永远没法跟翠婶比。从地里回来后,爹得先卸了青草,再喂牛,临了才能烧火做饭,他也不知道,到那时我的肚子已经饿得敲锣打鼓了。翠婶看我可怜,有时会让三奴奴拿一块南瓜或者嫩玉米棒子过来,给我充饥。这时我才知道,有娘是多么好啊!有娘不仅可以睡在软绵绵的怀里,还可以做饭。三叔每天做的营生和爹差不多,可他做完营生就能吃现成饭,哪像我爹呀,还得洗手做饭。那时我就想,如果让翠婶做饭,爹和三叔一起做营生,我们成了一家人,那有多好啊。如果那样,翠婶也有了儿子,三叔也有了儿子,三奴奴叫我哥,我叫大奴奴和二奴奴姐,叫翠婶娘,叫三叔……我突然想到该叫三叔啥呢?叫翠婶娘,就得叫三叔爹,可已经有爹了,总不能有两个爹吧,唉,那就不叫三叔爹了,反正他也不愿意理我,我叫他爹也叫不亲,我要的是能做饭的娘。
小牛进我家大门时,猛地颠了一下,一下子将我颠醒过来。我知道,这是我胯下的小牛急着要吃老牛的奶哩。这家伙一看到它娘卸下青草车子,就猴急急地想把我从它的背上摔下来。
爹将我从牛犊子的背上抱下来,嘱咐我进屋去,便自去卸那车青草了。我进了我家土屋,屋子里光线很暗,我却能准确地知道我家东西的位置。水瓮下面放着爹的笛子,爹说笛子发干了,会开裂,只有放在水瓮下面才能保存完好。爹在闲闷的时候就坐在门槛上吹笛子,笛子声音悠长,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我拿出爹的笛子试着吹了吹,可怎么也发不出声来。我去烧火圪崂找出自己藏在里边的纸元宝,这是拿爹的香烟盒叠成的方形纸片,我们叫纸元宝,拿去能和三奴奴姐妹赌输赢。我将纸元宝放到平地上,三奴奴拿她的纸元宝使劲拍一下,如果我的纸元宝被拍得翻了一个跟头,那么我的纸元宝就让三奴奴赢走了,如果没有拍翻,我就可以用我的纸元宝去拍她的。每到这时,我们都将自己的手臂甩得发酸发麻,可为了那个小纸片,我们都乐此不疲。可惜现在三奴奴大约在吃饭,没人陪我玩。我只能将那一沓沓纸元宝翻弄出来,按照新旧顺序摆在炕上,就像一个将军在检阅自己的士兵。
屋子里完全暗下来,可爹还没有卸完青草。我躺在土炕上,听到风箱圪崂里耗子扑楞楞跑过的声音,也有屋子外传来的牲口的嘶鸣声,当一切响声归于平静后,耳朵里却隐隐响起了滋滋若有若无的声音,整个屋子便显得空旷而寂寥。等爹卸完青草做饭时,我已经一个人躺在炕上睡着了。爹叫我吃饭的时候,屋子里已经点上了灯。
爹做的是酸稀粥,我委实是饿坏了,端起碗就猛吸几口。爹说,不要呛着了,慢点喝,又拿一碟酸菜给我。我照例夹一筷,将酸菜和到酸稀粥里,没头没脑地喝起来。
翠婶来了,她走进我家院子时,我就能听出她的脚步声。她又为我拿来了她家的老南瓜。看到翠婶手里的东西,我便跳下炕,从翠婶手中接过了碗。
翠婶说:我那娃就爱吃这东西。
爹说:你们吃吧,给他拿啥?
翠婶嗔怨道:娃是我的干儿子,爱吃就多吃点。
爹就不做声了,闷闷地喝稀粥。
翠婶抚摸着我的头,又说:多好营务的娃呀,给点吃的就行了。说完了,就看着爹吃饭的样子。
晚上我早早地就依偎在翠婶的身边睡着了,爹和翠婶有一搭没一搭地拉话。等我再次醒来,爹和翠婶仍旧说话,但我已经不在翠婶身边了,睡在了自己的被窝里,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脱的衣服。反正光不溜球地躺着,听到翠婶说话的声音仿佛带着抽泣。
翠婶说:那么多好女子哪个不比我强,你就找一个吧。
爹说:强不强我知道,能守着你过日子,娶谁都没意思。
翠婶叹口气说:这是造哪门子孽呀,看见你拉扯个娃过日子,我就愧得慌!
爹说:愧啥呀,我都习惯了。
我被尿憋醒了,我不知道翠婶为什么抽泣,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,就一滚碌爬起来,下地找尿盆。爹便从炕上爬起。我这才看到,爹和翠婶挨着躺在炕上。爹看着我尿完,就催促我快点睡。翠婶却一直躲在灯影里,也许是怕我看到。其实我才不管他们的事呢,翠婶和爹说话的声音,就是我的摇篮曲。
我们这个村叫老牛湾,老河在我们村子周围七拐八拐地绕了好几个弯,最后将我们这个小山村包围在三面临河的山坳里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村子里的人突然间慢慢变少了,石板街向阳的地方,除了几个扁嘴的老人外,再也找不到一个人影。要说家家户户还算完整的话,就剩我家和翠婶家了。我家虽说只有我和爹俩人,可从我记事起,我家就没有过别人,我和爹就是一个完整的家。翠婶家人多热闹,可平日里大奴奴和二奴奴都去了镇上的学校念书,家里只剩下翠婶、三叔和与我一般大的三奴奴。因此,要说热闹,还是我和三奴奴在一起玩的时候。我虽然不太喜见那个刁嘴的小丫头片子,但我却再找不到一起玩耍的伙伴,也只能凑合着和她玩了。好在我喜欢翠婶,翠婶也爱逗我俩玩,可这个小丫头片子,只要翠婶在场,她就想踩着我的肩膀上头,甚至想在我的头上撒一泡尿。
爹差不多喂着十头牛,夏秋两季爹除了在老河对面的山坳里放牛,就是收割满山的青草,将青草贮藏起来,到了冬天,那十头牛就窝在牛栏里咀嚼发黄的草料。翠婶家养的羊多,因此,三叔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梁上放羊,有时为了不跑远路,夏天里他几天也不回村一趟。他们有时也割青草,但青草大多是三叔背回来的,只要翠婶去割草时,草多的像小山一样,爹才驾着我家那辆破牛车去帮翠婶将青草拉回来。那时,我总是和三奴奴坐在牛车上,一起去拉青草。牛车一颠一颠的,还吱吱扭扭响个不停,这时三奴奴就乖乖地坐着,再也不敢上我的头了。
果真像爹说的,昨天傍晚天烧了一大片,第二天的天气就格外的好。爹没有带我到地里拉草,他要将几天里拉回来的青草晒在晒场上。我一个人爬上牛槽,看牛慢悠悠地倒嚼,二岁的小牛就用它长长的舌头舔我的脚丫子。我就坐在牛槽的沿上,任它来舔。爹担心我一个人去河边瞎溜达,就叫二奴奴过来和我一起玩耍。我也不知道爹只是去叫三奴奴,还是去叫翠婶和他一起晒青草。反正那天翠婶也带着木杈和爹一起去了晒场。三奴奴看着小牛舔我的脚丫子,也嚷着要爬上牛槽,爹就将她也抱了上来,安顿我和三奴奴只能在院子里玩。
那天,我和三奴奴尽情地享受着小牛舔脚丫子痒痒的感觉,三奴奴怕痒,小牛每舔她一下,她都嘻嘻哈哈笑个不停,我看到她笑得变了形的脸觉得她也怪可笑的,也哈哈大笑个不停。我俩的笑声惊吓了正在牛栏里刨食的鸡群,公鸡警觉地叫了起来,它的叫声显然让母鸡们不安起来,也跟着咯咯地叫着。我和三奴奴就冲着惊叫的公鸡母鸡乱喊乱叫,鸡吓得四处飞跳,将整个牛栏扇的黄尘飞舞,我俩嘴里都是牛粪的味道。
我和三奴奴再不能在牛槽玩了,就跳下牛槽,出了牛栏。我很想到河边玩,那满河哗哗流淌的水,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,可想一想刚才爹的交代,我只能叹一口气了。爹平时对我软绵绵的,可脸沉下来,也怪怕人的。因此我只能站在大门口的石坡上远远眺望河上升腾起的雾气,百无聊赖地和三奴奴去了晒场。
秋日下的晒场光溜溜的,比我家的土炕还要平整。每年还没立秋,爹就光着膀子将晒场上的野草清理得一干二净,然后从老河里挑几担水泼到晒场上,等水差不多都渗到地里,就赶着牛拉着碌碡压场,将晒场压得瓷瓷实实,就是我和三奴奴垫着脚在晒场上乱蹦乱跳,晒场也不会有一丁点泥土被带起。我家的青草和莜麦垛子占据了大半个晒场,高高的像一座座山丘,整个晒场仍旧弥散着那种青草的味道。我和三奴奴也不管爹和翠婶是不是在晒那一堆堆青草,就爬到青草堆的顶上,然后又从草堆上滑了下来,这种滑草的游戏,远比刚才小牛舔脚丫子刺激。我每一次从草堆顶上滑下,就仰头看蓝天上的白云,那云朵比夕阳下的云彩更有形状,我就觉得那是一堆堆棉花,如果我能从那一堆堆棉花上滑下来,那种飞翔的感觉一定比从草堆上滑下更令我陶醉。那天,我俩也不知道滑了多久,反正将好几堆青草都推的平平的,就像河滩上漂浮的绿藻。
就在我俩玩得兴致高涨时,我突然听到草堆后面传来一种怪怪的声音,像老牛在倒嚼。我问三奴奴听到了什么,三奴奴就竖起耳朵听那种声音。她本能地喊了一声:娘!那种声音就消失了,她又喊了一声,草堆后面就传来翠婶应答的声音。三奴奴又恢复了刚才兴高采烈的样子,说:是我娘和你爹。我也兴高采烈起来。
三奴奴就说:肯定是你爹和我娘又在一块偷吃东西了,你爹的嘴里一股烟屎味,太臭了!
我说:你爹的嘴才臭呢!
三奴奴说:我爹的嘴臭,可我娘不让我爹挨她。
我说:你娘夜里就搂着你一个人睡,你嫌臭,不能不挨你娘!
三奴奴说:哼!那也不让你挨!
爹和翠婶从草堆后面走了出来,我看到他俩手里拿着挑草的木杈,脸上笑盈盈的,一点也不像三奴奴说的那样。翠婶见我和三奴奴将草堆推得乱七八糟,就笑着骂我俩捣蛋,爹就将那些草用杈子铺得匀匀的。
在秋日的阳光里,爹和翠婶一杈一杈地挑动着那些青草,草上的叶子在木杈上四处飞舞,像舞动的蝶群。爹和翠婶边挑边相互看着对方,那舞动的蝶群将他俩包裹在里边,他俩又说着什么,翠婶不时地轻轻地笑出声来,她的笑脸在蝶群里灿烂而妩媚。
我和三奴奴终于玩腻了这种滑草的游戏,也不管爹娘在晒场上干活,自顾又回到了院子里。我俩拿出了各自的纸元宝。三奴奴说,拍元宝,应该到石板街的巷子里,那里有光溜溜的大石板,在那上面拍元宝,才能翻过跟头来。于是我俩就离开院子,去了石板街。
石板街的阴凉下,坐着大约有四五个扁嘴的老人,他们用手挡在额头上,远远看着我和三奴奴从村东头走过来。阳光打在他们核桃壳一般的脸庞上,一种古铜一样的颜色在他们脸上泛着熠熠的光泽,他们一脸慈祥的神色,让我和三奴奴觉得和蔼可亲。尽管我俩弄不明白那几位老人怎样称呼,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家的老人,但我俩在他们面前仍旧兴高采烈哼哼唧唧雀跃一般行走。
一位老人就说:这不是三扁头和二欢子家两娃吗?
他说出了我爹和三奴奴爹的名字。
三奴奴嘴快,抢着回答:我是二欢子的三闺女。又指指我说:他爹是三扁头。
我脸一红,就拿拳头捣她。我觉得这丫头片子也太多嘴了,而且还敢提我爹的绰号。三奴奴也捣我一拳,就笑着跑开了,还故意三扁头三扁头叫个不停。
我听到另一位老人发出感叹:哎呀,三扁头抱养的娃倒长这么大了!
那位老人又说:要不是二欢子家那女人,三扁头早娶亲了,也不会抱养这娃了。
又有一位老人问:三扁头铁了心不娶老婆了,要不才四十来岁的人,咋会抱养个娃娃呢?
另一个说:二欢子家那女人也不劝劝!
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我和三奴奴的爹娘,可我却听不明白他们的话,我看到三奴奴已经跑到石板街的巷子里,就撒欢似地追了过去。
秋日的巷子里有一股潮湿的气味,石块垒砌的矮墙下长满了狗尿苔和芨芨草,棕褐色的碱土从墙缝里剥落下来,间忽有一两只黑色的甲壳虫蠕蠕爬过,在碱土上留下细细的足迹。我和三奴奴那天的兴趣主要在拍纸元宝上,这丫头片子像发了疯似的甩着手臂,一会儿工夫就将我手中的纸元宝赢走了一沓。这很伤我的自尊,我变着法子不让她拍到我的纸元宝。我俩原本在光洁的石板上玩,后来我就将纸元宝放在了甲壳虫爬过的碱土面上,这样她就是有再大的力气,也拍不翻我的纸元宝。三奴奴就嫌我耍赖,嚷着不和我玩了。我就死皮赖脸地说,要是不玩,就把赢走我的纸元宝还我。她当然不肯,我就催促她快拍。这丫头片子鬼精,也将纸元宝放在碱土上,说,我不拍,你拍吧!我知道拍不过去,就悻悻地拿起纸元宝,说:不玩了!
我和三奴奴往家里走的时候再没那么欢实。我心里一直惦念着她赢走我的纸元宝,她好像也看懂了我的心事,郁郁寡欢地跟在我的屁股后面。经过那几个老人时,他们仍旧兴致盎然地议论着爹和翠婶。
一个老人说: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,那灰小子三扁头还在村里耗着,看能耗出个甚来?!
另一个说:人家养了好几头牛,那牛也值钱哩,比出去打工强。
一个就又说:那牛还不是给二欢子家那女人喂着,他就是把牛喂烂了,还不是填了那女人的无底洞!
其他老人好像就听出了别的意思,就呵呵地张开没牙的老嘴笑个不停。
那一阵,我就听到屁股后面的三奴奴“哇”地一下哭了,她哭得很伤心,就像谁猛然间踢了她的屁股。我被她的哭声吓了一跳,一脸惑然看她,她也不看我,一个人不管不顾地哭着跑回了家。
等我到家时,爹已经开始做上午饭了。爹沉着脸问我,去哪儿玩?我说我和三奴奴去石板街拍元宝了。爹又说,你欺负三奴奴了?我说没有。我还分辨说,她赢走了我一沓元宝呢,还有脸哭?!爹就哼了一声,沉着脸继续做饭。
那天下午,从翠婶家传来一个坏消息,翠婶和三叔打架了。三奴奴哭着来找我爹,说她爹揍了她娘一记耳光,她娘的脸都被打肿了,娘哭着说要和爹离婚,她爹就又把她娘摁在柴禾圪崂里打。三奴奴哭着让爹去拉架。爹听了三奴奴的话,提了一根烧火棍就怒气冲冲的出了门。我看着哭成泪人的三奴奴,就不忌恨她赢走我的元宝了。也拉走她跟着爹跑出了门。爹跑到翠婶家的大门口就止住了脚步。那时翠婶已经坐在她家大门道的石坡上抹眼泪,看着我爹手提烧火棍一脸怒气地跑来,就站起身来。
爹问:他打你了?
翠婶说:你来干啥,你快回去吧!
爹说:他要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,我就捅了他!
翠婶说:与你有甚相干,你快走吧!
翠婶说着就拉三奴奴过去,一声不响地关上了院门。
爹久久地站在翠婶家的院门下不肯离去。我竖起耳朵听翠婶院子里的动静,也听不到打架叫嚷的声音,就很认真地对爹说,他们不打了,我们回去吧。爹这才回过神来,狠狠地将烧火棍丢在大门外的荒草里,也不理我,闷头闷脑地转身就走。
那之后,我每天跟着爹去放牛割草,翠婶再没有来我家,我也再没有吃到翠婶家的老南瓜。只不过每天黄昏吃罢晚饭,爹总要拿出那枝笛子,蹲在门槛上一直吹到点灯时分,笛子的声音很低沉,呜呜的,像哭一样。
天气转凉后,我们老牛湾的山渐渐清秀起来,老河里浑浊的水也清澈了许多,街巷里更冷清了。那些老人们只有等到天气暖和的时候,才到石板街向阳的墙下晒太阳。我仍旧和三奴奴玩,只不过是三奴奴来找我,我却从来没有去翠婶家找过三奴奴。因为不知咋的,每当我走到翠婶家的院门下,我就会想起爹那天恶狠狠的眼神,我也同时想起了三叔那张冷冰冰的脸。
也不知过了多久,有一天翠婶终于又一次出现在我家的土屋里。那天翠婶抱着一大叠衣服,有爹穿的衣服,也有我穿的衣服,还有翠婶为我爹织得一件毛衣,为我织得一件羊毛袜子。翠婶再次抱起我,但这次她没有将我放在她的肚皮上,而是将那双羊毛袜子给我试了试,又不断地用手撑开袜子的腰子,好像生怕老羊毛扎了我的脚丫子。她边给我试着袜子和衣服,边和爹说着话,我看到翠婶脸上的泪痕,也闻到了满身的寒气。翠婶试完了,就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,又抚摸着我的脸和耳朵,她问我,你以后还记着干娘吗?我说,我记着。翠婶就在我额头上轻轻亲了一口,我感到她的嘴唇冰凉冰凉的。翠婶和爹说了好长一阵话,我看到翠婶又哭了。爹却抱着头,不做声,只是闷闷地抽烟,将我家土屋熏成了烟雾缭绕的神仙洞。
再之后时间不长,翠婶一家卖了所有的羊,就全家搬到了镇子上供大奴奴和二奴奴读书了。
爹和我一直住在土屋里,冬天渐渐来临时,我和爹就不去放牛了。爹将晒干的草铡碎了。撒在牛槽里,让牛在栅栏里吃草。没人和我玩,我就独自趴在牛栏上看牛儿吃草倒嚼。牛嚼一下,我也跟着嚼一下,牛将嚼碎了的草咽了下去,我也跟着咽口唾沫。牛的胃子里“咯鼓”一响,一团圆圆的东西从牛的脖子里游到嘴里,牛继续嚼着,我也试着能不能将东西翻到嘴里,但伸了半天脖子,还是失败了,只能继续跟着空嚼,然后再咽唾沫。
每天早上,爹都要做两件事情。他将我家的院子清扫的干干净净,将那些牛粪鸡屎之类的东西都倒到了墙外的粪堆上,又拿着扫帚去翠婶家的大门道,将那里的落叶荒草清理的一干二净。他清扫完街巷后,就呆呆地看着翠婶家的院子发愣。黄昏时分,爹照样吹那支笛子,我和那十头牛是爹的忠实听众,爹也不管我们能否听懂,慢慢地吸着气,将笛子的声音吹得悠长而缠绵。
我有时觉得冷清,就对爹说,我们也搬家吧,也搬到镇子上去。爹说,等你到了念书的时候就搬。我就问爹,为啥现在不搬?爹就闷闷地想上半天,然后少头没脑地说:为啥?就为守这条河哩!(完)
作者简介:岳占东,1973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五寨县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2014年定点深入生活作家、鲁迅文学院第22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?大地副刊》《文艺报》《黄河》《山西文学》《芒种》等报刊,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躁动岁月》《今夜谁陪你度过》、长篇小说《厚土在上》、长篇纪实《西口纪事》《黄河边墙》《鲁院时光》。曾获《文艺报》作品奖、全国校园文学作品奖,两次入围赵树理文学奖等。现为河曲县文联主席,兼任山西省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,忻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,走西口研究会副秘书长。
